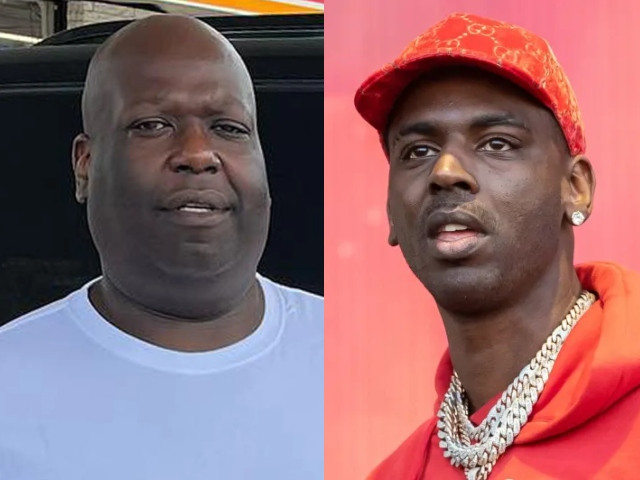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经常收到有兴趣申请我们课程的未来研究生的请求。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也有不少这样的要求。然而,最近有一群新的人开始向我伸出援手。这些是教职员工的同事——他们已经在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找到了工作——他们渴望以博士后研究员或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我们的项目。有些人在该国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大多数人都很坦率地表示,希望这将成为一种永久的东西,并给他们一个在国外重建事业的机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类请求的数目在过去一年中大大增加。
虽然经济状况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那些与我接触的人(以及我交谈过的其他人)普遍认为,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门没有真正的未来。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员工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按时领到工资。需要紧急修复的办公室和建筑物依赖于他人的善意和慈善。
教职工同事的沮丧不仅仅是因为历届政府的财政削减。HEC似乎也没有远见。一个本应为研究设定国家愿景的机构,往往对学位认证和陈腐的研讨会更感兴趣,而不是对研究和探究的实际支持。HEC在过去20年里进行的各种实验——从引进收取高额工资但却无法创造任何知识的外国教师,到各种丑闻,再到在首相官邸创建大学的奇怪想法——继续侵蚀着人们对该机构的信任。今天,两种并行的大学教师制度(BPS和终身教职制度)陷入混乱,导致教职员工进一步受挫。考虑到当前的社会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学科,但长期以来,人文学科一直被认为是教育体系的一个丑陋的继子。全国各地的大学领导职位要么空缺多年,要么被出价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人占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师意识到自己的职业阶梯被夺走了,这并不奇怪。离开的愿望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每个大学教员的离开都增加了留下来的人的负担——或者大学变得更加依赖(收入微薄的)兼职教员,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像正式教员那样与学生产生同样的联系。
不难看出,当前的模式——预算年复一年地削减,只能靠乞求、恳求和罢工来维持——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采取一些严肃的措施。HEC赞助的另一场关于质量保证和指标的研讨会并不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关于辛迪加的没完没了的法庭听证会,以及大学里不合时宜的晋升,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提出最基本的问题——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在这些夸夸其谈之外,国家高等教育是否有一个真正的使命(难道不应该有吗)?
在唯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是否有足够的选票来通过数量不详的高度可疑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过去类似活动的灾难性后果中吸取一两件事。好吧,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历史——特别是人文学科,关心高等教育——也许更多的人会知道,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处境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拥有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
像我的许多同事一样,我经常收到有兴趣申请我们课程的未来研究生的请求。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也有不少这样的要求。然而,最近有一群新的人开始向我伸出援手。这些是教职员工的同事——他们已经在巴基斯坦的大学里找到了工作——他们渴望以博士后研究员或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我们的项目。有些人在该国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大多数人都很坦率地表示,希望这将成为一种永久的东西,并给他们一个在国外重建事业的机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类请求的数目在过去一年中大大增加。
虽然经济状况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那些与我接触的人(以及我交谈过的其他人)普遍认为,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部门没有真正的未来。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员工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按时领到工资。需要紧急修复的办公室和建筑物依赖于他人的善意和慈善。
教职工同事的沮丧不仅仅是因为历届政府的财政削减。HEC似乎也没有远见。一个本应为研究设定国家愿景的机构,往往对学位认证和陈腐的研讨会更感兴趣,而不是对研究和探究的实际支持。HEC在过去20年里进行的各种实验——从引进收取高额工资但却无法创造任何知识的外国教师,到各种丑闻,再到在首相官邸创建大学的奇怪想法——继续侵蚀着人们对该机构的信任。今天,两种并行的大学教师制度(BPS和终身教职制度)陷入混乱,导致教职员工进一步受挫。考虑到当前的社会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学科,但长期以来,人文学科一直被认为是教育体系的一个丑陋的继子。全国各地的大学领导职位要么空缺多年,要么被出价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人占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师意识到自己的职业阶梯被夺走了,这并不奇怪。离开的愿望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每个大学教员的离开都增加了留下来的人的负担——或者大学变得更加依赖(收入微薄的)兼职教员,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像正式教员那样与学生产生同样的联系。
不难看出,当前的模式——预算年复一年地削减,只能靠乞求、恳求和罢工来维持——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采取一些严肃的措施。HEC赞助的另一场关于质量保证和指标的研讨会并不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关于辛迪加的没完没了的法庭听证会,以及大学里不合时宜的晋升,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提出最基本的问题——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在这些夸夸其谈之外,国家高等教育是否有一个真正的使命(难道不应该有吗)?
在唯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是否有足够的选票来通过数量不详的高度可疑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过去类似活动的灾难性后果中吸取一两件事。好吧,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历史——特别是人文学科,关心高等教育——也许更多的人会知道,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处境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拥有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